很多学者认为“易道”阴阳之学乃是儒道两家的共同源头,阴阳学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刚柔并济的宇宙观,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想人格的核心阐释。
这样的说法,可以认为有道理,因为这样的说法符合“易道”思想,尤其符合汉代以来的“传统”易道文化特色。然而把道家思想归之于“一阴一阳”中的“阴”,却是穿凿附会之说。
所谓“道家崇阴”,其实是“知其雄,守其雌”的必然选择
道家文化一路走来,不断蜕变,到老子时期才真正定型,并为先秦诸子所宗。
比如天下第一所国立高等学府兼政府智库“稷下学宫”,其教学主导就是“黄老之学”,学宫延续到秦灭六国。但学宫的开放性使它并不排斥任何学说的交流,比如孟子荀子都曾担任过“稷下先生”。
历史上“以老解易”,即以道家思想诠释《周易》的,最终形成易学重要一支——“义理学派”。而“以易解老”的却往往偏离甚至曲解老子之道。
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,极少提到“易经之学”,《论语》涉及到“易”的只有一句话,还是关于“易占”方面的内容。
同时,坚持易道说的,误会了老子“正言若反”的道理,以为道家主张“清静、无为,柔弱、居下、不争”,就将其归于“阴”,这种说法极不严谨。

事实上,道家所揭示的大道属性,看似柔弱、清静、无为、不争,实则是雄强的、顶层的、强者的自觉选择。
而这种行为方式存的前提是“知其雄,守其雌”,就是说“清静无为”的前提是“雄强”的,就像父母慈爱幼儿一样,出于对“子女”的“慈”、“俭”、“不敢为先”的强者,体现出的却是慈柔的一面,这是生机活力的象征。
故曰“坚强者,死之徒也;柔弱微细,生之徒也。兵强则不胜,木强则恒。强大居下,柔弱微细居上。”逞强者,非长久之道也。
下面简单分述大道属性。
清静强调的是权力的非暴力行为,即不扰民
“清静”与“无事”近义,清静是大道的根本属性之一,“静为躁君”,“静”是事物之根、之本,故曰“归根曰静”,换言之,静即是归根,权力不静,则意味着邦国伤根动本。
相对于万物,道为根、为源、为母,是静态的;万物为末、为流、为子,是动态的。道静,则不烦扰万物,万物也终将归于静。
《老子》说:“躁胜寒,静胜躁,清静为天下正”,又说“牝恒以静胜牡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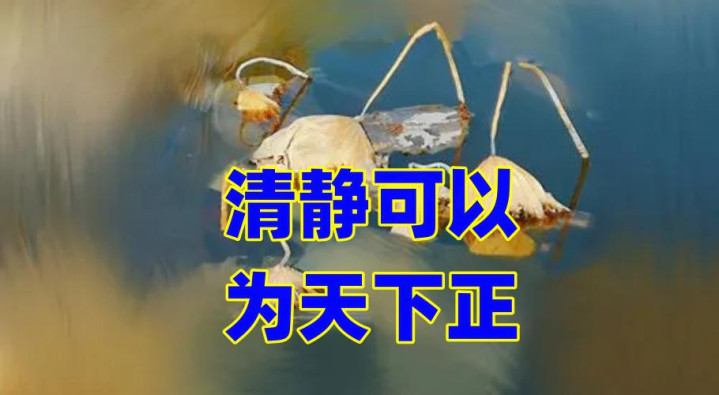
道虽至尊,却不自以为尊,能清静不扰物,则物自然而得全性,躁则犯物之性,所以圣人谨慎行权,清静不扰民,才能“民乐推而弗厌”,成为百姓之首领。
就像父母对待子女,顺其本性,助其成长,为辅不为主,不试图强力控制,故能为子女所尊重,正因为父母的伟大,才表现出慈柔的一面。只有怯懦,才会示人以强势的一面。
“牝恒以静胜牡”是对“静胜躁”的比喻,雌性相对于雄性是处静的,雄性总是躁动的,以此比喻权力守静才能天下安定,权力狂躁,则会带来天下大乱。
所以,圣人为政清简,不生事造作而劳民伤财,不扰民侵利,民心安,则天下平。
柔弱强调的是权力慈柔不行暴政
天下之大,大不过道(域中有四大);天下之强,强不过道(天网恢恢疏而不失)。然而强大如斯的大道,对于万物却是“弱者道之用”。
大道对万物的作用形式是间接的、辅助的,非主导和强力的,故曰“柔弱”。道家的“三宝”第一宝就是“慈”,慈就是慈柔,就是“弱用”,比喻权力“方而不割,廉而不剌,直而不绁,光而不耀”。
也就是“挫其锐,解其纷,和其光,同其尘”,不是大道要“挫”物之“锐”,“解”物之“纷”,而是大道自身不带锋芒,不伤物、刺物,不惊扰万物,也就是权力不伤民、害民。

“柔”是生机的象征,“弱”是大道的作用:强大者、权力者,为政却是柔弱的、非威权的,即“邦利器不可以示人”——公权力不能对民众耀武扬武。
故曰“守柔曰强”,真正强大的,却是守柔而不以“强”示人的,而依靠暴力威慑民众使其就范的暴政,其结果只能是“强梁者不得死”,因为权力这个“鱼”脱离了民众这个“渊”,所以有道权力“不以兵强于天下”。
“不争”不是与世无争的庸俗处世哲学,而是权力不与民争
所谓“不争”,指的是大道(圣人)的自然属性:“万物作而弗始也,为而弗恃也,成功而弗居宰”,在功名利禄方面“退其身”“外其身”,“不敢为天下先”。
是大道不与万物争,为道的圣人不与百姓争,是“天之道利而不害,圣人之道为而不争”,而不是世俗文化的“与世无争”。圣人不与民争,故“天下莫能与之争”,民心所向,谁能争过圣人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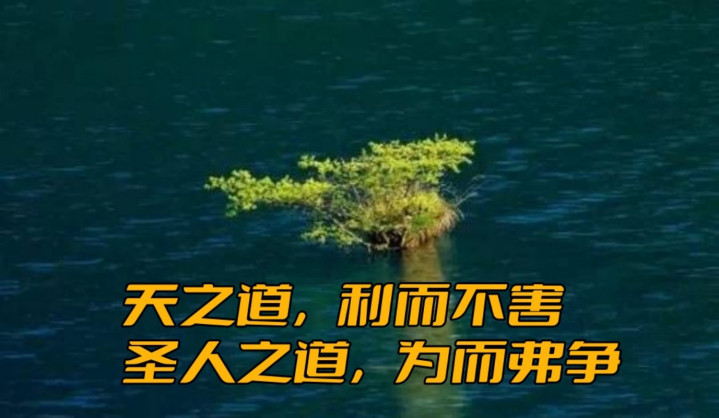
《道德经》是客观陈述事实,揭示事情真相,不是道德说教文化,不是庸俗处世哲学。
“无为”才是“清静不争”的重中之重,也是“道法自然”的必然要求
“清静”、“柔弱”、“处下”、“不争”、“无事”等等所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思想,即“无为”,换言之,这些大道的属性都可以“无为”来概括。
就是说,大道(圣人)清静、柔弱、无为、处下、不争,都是对“无为”思想不同层面的表达,属于“无为”的“族概念”,它们都是大道对万物“弱者道之用”的不同层面的论述。
老子论道得出结论说“道法自然”,即强大的大道尚且要以万物之自然为法则,惟道是从的圣人当然要以百姓之自然为准则。
所以,老子提出“无为”主张,最终目的就在于“法自然”:不干涉、不损害万物(百姓)之“自然”,反对外力强行干涉,破坏万物整体自然和谐与稳定。
“无为”就是大道(圣人)“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”——“能辅”和“不能为”,就是大道具有“辅助”万物的能力,但却不能“为”:为者败之,执者失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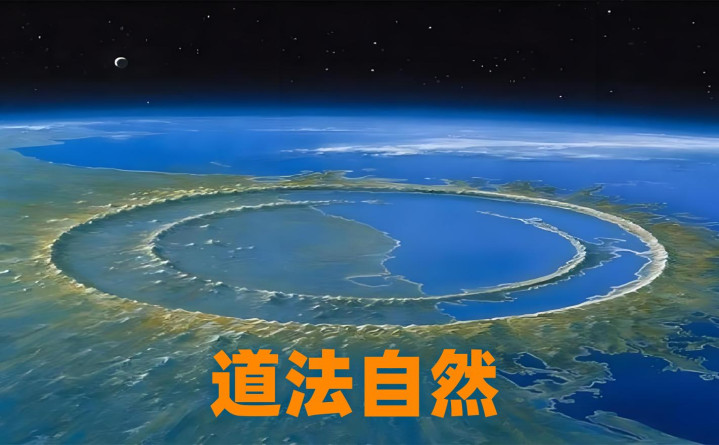
那些动辄说:看了你“无为就是不做”的说法,就知道你根本不知“道”,请允许我回敬一句:如果“无为”仅仅是一种个人修行,一种“做事的态度”,一种“一切烦恼永尽的无为法”,那么,你就把老子跟佛陀等量齐观了。
不是说老子高于释迦牟尼,而是说,老子强调的是施政行为方式,佛陀强调的是灭除烦恼之法,两者不可同论。
所以,老子的“无为”就是“不做”,特指圣人或现实统治者不做干扰民众自由发展意愿、侵夺民利的事,不做“天下多忌讳”、限制民众“自化”、“自富”的事;不做“取食税之多”盘剥民利的事,等等。
总之,“无为”就是权力辅助民众自由意愿,让民众放开手脚,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各施所长,各得其所,实现“无不为”。
只有权力者“无为”不干涉,天下人才能在没有强行干涉的情况下,实现“无不为”。因此老子说:“我无为而民自化;我好静而民自正;我无事民自富;我欲不欲而民自朴。”

